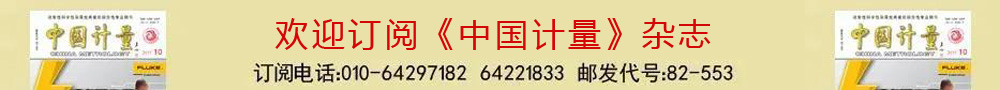光學家王大珩光耀中華 (2006-02-23)
發(fā)布時間:2007-12-04
作者:
來源:央視《大家》
瀏覽:1031
開場白:
在新中國的科技發(fā)展史上��,有這樣幾個標志性的事件:1956年國家科學發(fā)展12年遠景規(guī)劃、1958年國家提出“兩彈一星”研制計劃、1986年我國為迎接世界新技術革命制定“863”計劃,以及前不久制定的我國科技中長期發(fā)展規(guī)劃等等����。在上述所有的這些事件背后�,都曾出現過一個科學家的名字,他就是我們今天要為您介紹的大家??王大珩先生��。
解說:
2005年底�����,在北京中關村的中科院家屬樓里����,我們見到了王老����。由于年事已高,他平常很少外出�����。王老現在的視力已經非常微弱,讀書看報主要依靠家里的這臺放大儀����。
訪談:
王大珩:我是2月22號的生日,2006年元旦距離我的生日呢是57天����,現在呢,加上現在����,今天是20再加上14是67天,現在是67天��。67天呢由365去除就點幾了����,不到點二。所以這樣子算起來呢��,我的歲數現在只是90.82��。
主持人:90.82��,您是不是做這個光學儀器,精密儀器���,做精密計量做慣了��,年齡也算得這么精��?
王大珩:腦子里面好像一過就可以說出來了�����。
主持人:但您現在看起來不太容易了���。
王大珩:現在看起來不太容易,要看也可以���,要看我這樣子看���。
主持人:每天您都掛著這個放大鏡�����?
王大珩:他們送了我一個閱讀器把字放的這么大�����,坐在這兒看,這個很方便�����,這個就可以看書�,現在我們看書,所以這幾年我光這個文獻上“去閱讀”這個話是空說了�。
主持人:現在閱讀,閱讀就比較困難了��。
王大珩:比較困難了��,有些東西����,就是有時候參加學術活動,靠耳朵去聽��,了解一些現代科學方面進展的大的形勢����。
主持人:你現在是不是非常急于想了解一些新的信息,新的知識��?
王大珩:好像這是我們也可以說,是本質上的一個使命�����。
解說:
使命這個詞似乎可以為王大珩一生的成就做一個注腳��。
1999年9月��,國家為在“兩彈一星”的研制中做出了突出貢獻的23位科學家頒發(fā)“兩彈一星”功勛獎章���。這是王大珩在公眾面前最公開最隆重的一次亮相�����。
四十多年前����,作為光學家�����,王大珩帶領近千人為兩彈一星的成功研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學觀測設備:用來測量中程地地導彈軌道參數的我國第一臺大型靶場觀測設備����;用來記錄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攝影儀;以及我國第一顆可回收對地觀測衛(wèi)星所用的對地觀測系統(tǒng)����。
直到今天,在我國“神舟”系列飛船的發(fā)射中��,王大珩當年帶領大家研制的光學電影經緯儀依然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在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那天�����,王大珩邀請了幾位同事一起慶祝�,席間,他說了一句當時大家誰也沒聽懂的話:“要是再晚半年就好了……”
半年前�����,王大珩的父親王應偉去世了�,父親一生抱著科技強國的夢想,卻沒能分享到兒子親自參與的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喜悅���。
王應偉是我國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氣象學家����,也是對王大珩一生影響最大的人之一。1915年王大珩出生在日本東京�����,那時父親已經留學日本八年了�����。
訪談:
王大珩:我出生的時候����,我父親已經在日本的氣象臺上大概待了兩年多了,我查了我父親回來時�����,1915年的夏天回來的�。那么在日本,我真正說起來我����,只待了六個月。
主持人:那您父親有沒有跟您談過為什么1915年的時候會從日本回到中國���?
王大珩:那個時候��,1915年是日本向中國提出21條的時候�,那時候覺得日本將來肯定是中國的大禍害��。
主持人:您父親也是因為這個離開日本�����。
王大珩:那時候就回來��。
解說:
父親給王大珩起的小名叫“膺東”�����,寓意就是滿腔義憤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父親一生始終認為只有靠現代科技才能使國家強大起來,直到現在王大珩還記得小時候父親講給他的科學故事���。
訪談:
主持人:您小時候你父親怎么教育您的�?
王大珩:也可以這樣說吧�,從小說起來,大概父親看見我還有點名氣���,所以是有點好像對于科學知識的這方面的培養(yǎng)��,有點有意識的把我向這個方面引導�����,比如我常記得一件事情�,說起來很簡單,一個筷子斜放在水里面���,你就看見那個筷子進水的時候彎了一段�����,就講這是叫“折射效應”����,就給我講這些事情�����。
主持人:您父親給您做這個小實驗小演示�,給您講這個故事。
王大珩:靠這種日常生活里面��,引導我往這個科學方面想這些問題。
解說:
1932年��,17歲的王大珩考取清華大學物理系����,雖然父親跟他說學物理會窮一輩子,但王大珩依然堅持了自己的選擇�����,因為他早就聽說清華大學理學院有著名的物理學家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等大師�。大學四年的時光讓王大珩受益匪淺�����。
訪談:
王大珩:這些清華的有名的教授對于我的人生觀上面����,給我很大的教育跟啟示。
主持人:人生觀方面����,還不光是學術方面�����?
王大珩:不光是學術方面����。
主持人:在人生觀上給您了一些教育�,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教育呢?
王大珩:這種很難說了����,給我們一種非常識大體,這小節(jié)方面很講道理���,不講人情�、不講私情����。
主持人:講道義不講私情。
王大珩:譬如說我們有一次為了某個學生�,這個學生現在也是很有名,就是于光遠�,他生活比較困難��,我們想是不是老師可以接濟他一些����,這個葉先生沒有答應�����,但是給他介紹了一個學校����,到他學校去教課。
主持人:給他一個工作的機會��,那就是這種“幫助”幫助得非常有原則��。
王大珩:非常嚴謹�����。
解說:
葉企蓀先生是王大珩最欽佩�����、最敬重的老師之一��?�?箲?zhàn)爆發(fā)后��,葉先生始終教導學生要認清自己的歷史使命��。老師深沉的民族大義和拳拳的愛國之心深深地震撼著年輕的王大珩���,一直到現在《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都是王大珩最愛唱的一首歌���。
訪談:
王大珩:我頭一次聽這段是在船上,因為我們一起從天津往南走的��,也有東北流浪的學生��,這個歌是從他們嘴里唱出來的����。
主持人:應該說那時您心中有逃難的感覺,被侵略者趕的��。
王大珩:那個時候聽了心里發(fā)冷����。那個時候抗戰(zhàn)在開始��,所以這個歌對我印象是很深的�,到國外時候�����,我們在同學面前還唱這首歌����,人家覺得我唱這首歌很有感情,這個感情是���,大家都是用一種愛國�、救國的心情唱這個歌的����,
解說:
1938年����,王大珩考取中英庚款公費留學資格。兩年后���,他獲得了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技術光學專業(yè)的碩士學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由于在軍事上的重要地位����,光學玻璃當時被西方各國視為重要的保密技術。為了學到這種中國還沒有的技術�����,1941年王大珩轉學到英國雪菲爾大學玻璃制造技術系�,跟隨著名的玻璃學專家特納教授學習。但是正當他著手準備博士論文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遇,讓他毅然放棄了即將到手的博士學位����。
訪談:
主持人:您在英國上學的時候還有一個對您來講很重要的選擇,就是您放棄了博學的學位�����,到英國的昌司公司去工作����,這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王大珩:在英國學習的時候,關于美國光學玻璃的發(fā)展寫過一本書���,從這里我了解光學玻璃制作的內容�,內容就是要通過些實踐����。我作為一個學物理的,這方面實驗知識知道一點�,工廠的知識是很少的,剛好碰見有這么個機會��,是那個昌司公司當時有一個實習員�,跟我同學我們關系很好。
主持人:是他介紹您去的���?
王大珩:是他介紹我去的���,因為學光學的人并不多����,那么在這種情況之下���,打仗的時候,要找個合適的人不容易�,而且要找個能力強的人更不容易。昌司公司老板呢����,他在英國還算是比較開明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接納我去了。
主持人:您當時去的時候���,您有沒有意識到這個工作對未來的中國是重要的�����?
王大珩:有那么點���,光學玻璃這個行業(yè)在國際上還是認為有一定,當時說是帶有一定保密性的���,我去的時候約法三章��,我不準進他們的車間����,只準在他們的實驗室里。
主持人:因為他們是保密的���?
王大珩:因為它是保密的����,盡管你不僅這個車間���,車間生產方面出現的問題��,讓你在這兒覺得這是給我一個機會����,一個很強的一個機會���。
主持人:所以當時你選擇了去昌司��,而不是再去讀那個博士學位�����,博士學位還是很重要的�。
王大珩:我當時看這個學位沒像現在看這個學位那么重�,我說這些工作可做可不做。
主持人:您那時候關注的是要去做一些事����。
王大珩:中國有一句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抱著這種精神去的���。
解說:
這是王大珩在英國留學時做的實驗筆記。在英國十年的學習和工作��,王大珩不僅掌握了許多當時保密性很強的光學玻璃制造的關鍵技術�,而且還研制出快速測量玻璃光性精確度的V-棱鏡折光儀,這為他日后回國開創(chuàng)新中國的光學事業(y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